生命伦理的现实难题 和而不同的应对策略 | 老游评书
《没人能是旁观者》
撰写 | 中华医学会 游苏宁
作者指出,生命伦理学是实践伦理学的分支,要协助医生、与健康相关的科研人员、公共卫生人员以及相关监管人员解决其面临的伦理问题。因此,必须了解与他们面临的伦理问题相关的事实,尤其是医疗中与新技术应用相关的知识及其特殊性,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出合适的道德判断。本书的副标题为“14个拷问人心的生命伦理难题”,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生命伦理最初的问题,资源短缺时该救治谁;是否可以给患者排定治疗优先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类选法;残疾新生儿面临的困境,接受还是放弃治疗;生与不生的两难,不让不幸的孩子出生和不当生命诉讼;断绝不良基因,《强制不育救济法》;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是否接受器官移植,自主决定以及孩子的权利;治愈无望时,美国的《自然死亡法》;尊严死与安乐死,尊严死运动;人生最终阶段的协商;脑死亡是否算死亡,出台《器官移植法》的意义;你愿意捐献器官吗?供体器官不足的尴尬;生命属于你吗?医疗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的生命;未来会怎样?科技的发展与我们所期待的世界。
英国诗人亨利的诗句“我是我命运的支配者,我是我灵魂的指挥官。”非常形象地诠释了生命对于人类的意义,每个人的生命都无法重来,喜怒哀乐中无不彰显个人的意识独立性。作者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新技术,以及形形色色处于不同文化和亚文化情景下的患者,仅凭单一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或“主义”是不够的。尽管我们负有尊重任何一个人的人格权、生命权和身体权的义务,但我们不能认为衡量一个人行为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在于是否行使了对人的义务而不考虑行动的后果,陷入“后果论”或“义务论”的泥沼。因此,在解决生命伦理学面临的问题时,必须采取多元的理论和路径,并将利益攸关者的价值加以合适的平衡或权衡。作者强调,解决当前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能仅靠科学家或医学家的独立决定。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他们并不拥有“自行裁量权”。在我国总结贺建奎事件教训时,也强调能否进行遗传基因组编辑技术,绝非可以由科学家、科学团体和科研机构决定的科学问题。只有科学和民主携手同行,才能解决新技术在医学应用上的伦理问题。
作者指出,尽管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但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一个“伦理时代”。“伦理”一词被频繁提及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社会无法按部就班地发展,人们因此而感到痛苦的时代。回眸史册,我们会发现每个“伦理时代”都是一个人类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发生动摇,人们不知该如何思考和生活的时候,就会求助于伦理。身处时代巨变期的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难以预测未来,而人们又不得不在这种不确定性中继续生活下去,此时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活在当下。本书就是围绕着被称为“生命伦理”的各种话题,尝试着用活在当下的角度去思考。作者认为,医学伦理的道理既不简单,亦不单纯,在百姓心中最为在乎的是公平与公正。在人的生命这一主题下,问题何在?人们寻求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人的生命,而这也是一切价值的根本所在。
俗语道,医院是人生喜怒哀乐的舞台,是坟墓的接待室。现代人的一生始终离不开医院,生于斯,死于斯,疗愈在此,其中尤以死亡最为纠结。尽管医学的进步一日千里,但它绝非万能之术,因此人类在与病魔的搏斗中,总应心存敬畏。每当科学家发明的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时,都会不断产生人们难以应对的新伦理问题。面对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难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医生;身处进退两难的困境,独自烦恼并做出决定的也是医生。医学专家需要从实际出发,对其进行具体的了解、分析和研究,特别要注意各自的特殊性,而不是靠思辨或已有理论的推演来解决。人生漫漫,从摇篮到墓地,迢迢3万天,但周期性降临的疾病、灾难、瘟疫、动乱都会干扰、改变其自然进程。憧憬死亡并非多余,而是必需。因此,每个人都应在健康时预立医疗指标,以应对突发死亡的伦理选择。作者指出,人生百年,终有一死,面对死亡无常,树立“有准备的死亡”观念,就是刻意培育豁达的生死观。作者希望死亡是有尊严的、温暖的、利他的,而非凄凉的、悲惨的,他所倡导笑对人生的姿态应该是“随时可死,处处求生”。
作为日本的医学伦理学家,作者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日本的标志性事件,也探讨了许多在国际上广受关注的跨国案例。尽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在生死观上差异明显,如国人常言“生死大事”,孔夫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但日本人的观念是“死生大事”,先言死,后言生,人生如同绚烂一时的樱花,要么怒放,要么凋零。尽管两国国民的生死观不同,但人们对医学、医院、医生的敬畏与感恩之情并无明显差异。作者指出,医患之间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一种信托关系,强调医患之间是契约关系就会改变“医本仁术”的本质。对于一个人来说,当治疗无望时,是否有权选择安乐死?选择的人多数饱受苦痛的经历,如老年痴呆、癌症、精神疾病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等,他们对亲人的不舍和不忍拖累形成了极强的对比。最终,很多人选择了主动羽化西去。对难以回天的患者,是永不言弃,生命不息,抢救不止,还是根据患者的意愿,适时放弃无谓的救治,让患者安静、安宁、安适地离开,这些都需要技术与人文统筹发力才能解决。
时至今日,脑死亡概念的辨析模糊了死亡的传统节点,认定死亡不再是依据某一个器官的功能丧失,而是多器官的衰竭,而且大脑功能丧失的权重大于呼吸、循环功能终止,这就为判定死亡和摘除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器官提供了新的时间和空间契机,也对何时终止植物人的支持系统提出了新的伦理挑战。生命指征微弱的有缺陷新生儿,已经成为新的临床伦理焦点,救与不救,都面临着伦理拷问。生育环境中的伦理问题丝毫不比死亡伦理简单。以上种种情形都有可能与我们中的某个人不期而遇,这是由于生命的偶然性和医学的不确定性所致,并非医生们不努力,而是疾病的演进轨迹太复杂,死亡的发生太无常。因此,王一方教授在序中坦言,医院里没有什么真相能大白,也没有什么妙手可回春,只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永恒的探索性,医学伦理不过是一份心理补救,为人类洞悉“生命盲盒”提供一份知行合理性的辩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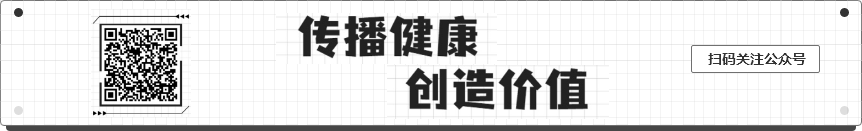
评论

推荐内容
